陈巍评《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人与马,共天下
- 外汇
- 3小时以前
0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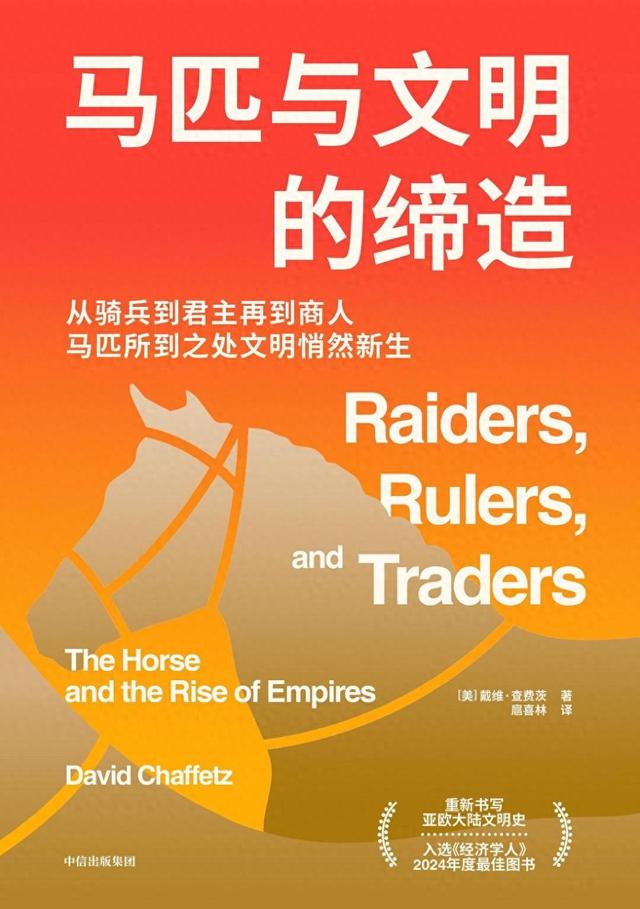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戴维·查费茨著,扈喜林译,社,2026年1月出版,440页,88.00元
英国学者戴维·查费茨(David Chaffetz)的新作《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以四百余页的篇幅书写了纵贯四万年、横跨欧亚大陆的人马互动的文明史。全书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马参与人类文明的长时段历程。作者提出理解欧亚历史的关键不只在王朝兴替,还离不开马这一关键动物提供的动力。出于定居文明对优良马匹持续存在的巨大需求,“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作“马匹之路”。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并不陌生,但查费茨不断在斯基泰、匈奴、契丹、突厥、蒙古等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国、印度、波斯等农耕文明之间跳转切换,充分运用对照和群体比较方法将纷繁复杂的史料串联成引人入胜的叙事,从而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欧亚大陆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和启发。
全书利用考古学、生物学、军事史和文化史等不同领域资料,对马在不同时段各种社会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例如,作者详述了马匹在草原经济结构中的不可或缺,这不仅因为它是食物、燃料和移动能力的来源,还在于它能够为牛羊等反刍动物提供保护和引领(20-21页)。与草原环境相比,农耕区的土壤看似肥沃,但雨水冲刷掉了硒、钙等矿物质,导致难以养出超过十三手高的马,哪怕它们是优良马种的后代(103页)。这导致农耕社会难以自给精良马匹,不得不长期向周边“文明竞争者”购马。又如,书中对战车与骑兵的技术换代也做出了解释:最初人类用于战争的是马拉战车,而非骑乘,这是因为早期的马体型小、各类装备尚不完善,随着嚼子、马鞍等各类马具得到改进,有目的地培育出可堪负重骑战的优质马种,真正的骑兵时代才正式到来。
作者引用古希腊、波斯、中国、蒙古、印度、土耳其等多种语言中有关马的词汇和典故,评析了历代文学和图像中对骏马的描述,不但为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提供了扎实的注脚,也让全书读来生动流畅。正如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在书评中所说:“这本书文字优美,结构清晰,每一步论述都有恰到好处的例证。”在农历马年到来之际,如此一部融学术深度与可读性于一身的佳作,无疑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

唐《牧马图》
笔者长期关注欧亚大陆范围内与马相关的技术知识传播,私下曾戏称“人与马,共天下”,马并不仅是被驱使的工具,更是与骑者合伙创业的“真堪托死生”的伙伴。在推荐新著之余,笔者也希望结合查费茨提供的资料,提出对欧亚大陆马匹知识传播的结构与动力的点滴思考。
从这本书的英文书名(Raiders, Rulers, and Traders: The Horse and the Rise of Empires),可以大致归纳出有关马的驯化、养牧、驾驭及评鉴等知识,主要在三类人群之间传播交流——游牧民族、定居农耕民族以及在二者之间充当桥梁中介的贸易者。这一组长期互动的“三体”,奠定了马匹知识流动的特点。
首先,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内部,马的知识天然地孕育和发展,并经由部落迁徙和征战迅速传播。
马在游牧社会中是生存和征服的核心,游牧民世代与马为伍,积累了最丰富的马匹驯养经验。如前所述,马是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平日里人们离不开马奶制品和马粪便,狩猎战斗时则能在“一马当先”和“打不过就跑”之间迅速切换。在长期适应互动下,骑战技能对游牧民个体而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人与马结成亲密的心理纽带,从而默会性地完成诸多马术技巧。但在历史视角下,这类技能又是渐进的,草原上曾涌现出复合弓、阉马骑乘、高桥马鞍、帕提亚后射术等二级创新,对于另一些改善骑乘条件的技术,如马镫、马蹄铁等,游牧民却因对骑乘过于熟悉,接受起来相对迟疑(154-155页)。当某一游牧群体取得新技术优势后,往往通过战役或日常移动传播到其他草原部落乃至远方。甚至马和游牧民族的身体都因长期骑乘发生变化:马患上关节炎或腰椎融合等疾病,人的股骨则因大腿和膝部长期用力而逐渐拉长。四千年前草原墓葬中这类伤病的存在,是骑马活动存在的证据之一(26页)。遗憾的是,除了在游牧农耕复合王朝,古代草原马匹知识很少通过文字系统地记录下来。
第二,对于中国、印度、波斯、西欧等定居农业文明来说,有关马匹的许多知识最初来自草原,然后在本地加以吸收、改造和发展。
几乎所有重视骑兵的农耕政权都曾主动从游牧者处获取马匹,并在借鉴外来知识后建立马政体系。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西亚的赫梯帝国就从草原招募了一位名叫基库里(Kikkuli)的战车教头。楔形文字泥板上留下了基库里的训练建议,其中的术语有不少与古代印度吠陀经中的词汇类似(47页)。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帝国也向游牧的米底人学习先进的马具和马术。对米底骑兵的过度依赖甚至酿成公元前612年米底人倒戈起义,攻陷了亚述都城尼尼微。这样的事例在后来的唐朝、马穆鲁克王朝等多次复现,揭示出马匹知识是融合一整套技术的“知识包”,在异质的农耕社会,它只能逐渐解压缩。当与知识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必要整体存在时,马匹这类战略物资对农耕社会实际上具有潜在的风险。
随着知识移植进程的推进,草原上粗粝的马文化在定居文化中得到增殖。原本简单明晰的英雄传说在波斯《列王记》等史诗中加入了更多细致的情节,而马匹的命名也从具象趋于意象。马匹知识在传播的同时与既有知识系统展开密切互动,例如充斥着神秘色彩但对养育良马实用价值有限的相马术(100页),以及脱胎于人的体液平衡学说的马匹喂养手册等(263页)。这种知识冗余的现象在农耕文化面对舶来品时十分常见。实际上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养马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这导致养马者经常敷衍了事。在承平时期,文人墨客们歌颂的往往是雍容的肥马、慢马。
第三,活跃于欧亚商路上的贸易者充当了马知识跨文化传播的中转站。
除了我们了解较多的中国古代历代马市外,中世纪印度也依赖从中亚和阿拉伯输入的军马。印度王公为买马付出大量金钱,令西亚和欧洲商人趋之若鹜,控制货源的波斯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先后组建跨海贸易网络。其中葡萄牙人最初为香料远赴印度,最终却靠垄断马匹进口使果阿港贸易繁荣,他们甚至改进了船舶设计以更好地运输马匹(270页)。马商走南闯北,不仅出售马匹,也传播着马的饲养与鉴别知识。若无娴熟的相马眼光,很可能在贸易中受骗,买到看似年轻的老马,或在马具中灌水假冒的骏马。幸而随着马匹贸易的持续开展,实用的相马术也在传播,而买卖双方的鉴定技能也随着双方博弈逐渐演进。贸易者的作用在历史上常被王侯将相所掩盖,但他们在知识交流中的润滑作用却不可忽视。查费茨注意到汉武帝在获知“天马”信息之后,边境商人踊跃请缨前往中亚采购,而他们的失败则成为耗费巨大成本远征大宛的前奏(114-115页)。
一些马具创新的传播,以往研究者多强调作战带来的“激发式传播”以及由此衍生的骑兵训练等军事交流途径,但也应看到,马镫、马铠、蹄铁以及华丽的马鞍,都需由工匠制作,而在专供皇家贵族的产品之外,贸易依然是它们在民间传播的必经渠道。在欧亚大陆尺度下,正如查费茨所说,“马匹之路”是各地买家和卖家共同走出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大规模国际贸易路线,让马文化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中得到共同推崇(第7-8页)。
我们以查费茨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可以大体描述不同层面的马知识在欧亚大陆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跨文化贸易框架中,优良马匹的生产者——游牧民族,和消费者——农耕民族,在文化接触初期如果直接深入彼此腹地,总是面临疑惑甚至恐惧,这种潜在的冲突风险的根源在于马的早期驯化所塑造的不同生业形态的分离。而要持续开展相对和平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必须借助贸易者的粘合润滑作用。

与马相关的知识在欧亚大陆不同群体之间传播的结构(使用Gemini 3 Pro绘图)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马知识传播的动力机制。马匹知识之所以在不同社会知识体系间流动不息,背后存在着各方面的动因。它们既驱动马匹知识的宏观结构中不同部分连接起来,又通过推动知识的再加工、博弈等融合进程,参与着不同部分的演化。这些动因可初步归纳为生态环境的差异、各文明因马的功用(特别是军事用途)形成的供需落差、商业逐利等。
首先,在生态环境方面,欧亚大陆各地悬殊的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马匹与其他近似功能生态位的动物之间的竞争,以及饲养和相关技术获取的必要性与发展方向。理查德·布利特曾对中东和北非环境下马匹与骆驼的竞争做出精彩论述,查费茨的书中则多次将马与同样可用于作战和运输的大象加以对比。印度大部分地方炎热、潮湿、森林茂密,不适合养马,拥有可怕战斗力和雄壮外形的大象则成为王权的象征。气候环境的长期稳定让印度王公认为仅靠大象就能打败骑兵。然而战马却拥有战象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规模化优势,这让历史上自信的大象拥护者们屡遭惨败。经过淘汰剩下的印度统治者转而宁可忍受不断进口马匹的沉重财政负担,也要让国家命运与来自草原的战马和骑兵深度绑定。与印度贵族不同的是,初出草原的蒙古人占领撒马尔罕后,放任那里饲养的大象自行到野外觅食导致它们全部饿死,这也显示出环境影响下的观念延续性(82-85页)。
定居民族精心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让马过得舒适,比起马的诸多优点,付出这些辛劳完全是值得的。定居民族帮助马匹适应不利环境而做出的种种技术改进,在游牧地区却显得可有可无。例如草原适宜马匹自由放牧,游牧骑手的马匹储备充足,很少给马钉蹄铁;相反,在崎岖山地或坚硬路面上行军,若无蹄铁保护,良马极易磨损受伤。正因如此,蹄铁这一技术首先在高句丽等多山的东北亚地区获得广泛应用,后续又传至河西走廊一带。

敦煌莫高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第二,农耕文明对马匹的精细管理无法弥补对优良马匹持续存在的巨大刚性缺口,造成不同文明间长期存在马的供需落差,并转化为近于先天存在的养马知识的势能差。
农耕文明在养马方面的生态劣势导致其马政经济成本居高不下,养马传统难以深入社会基层。出自农耕地区的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支撑国防需求,几乎只能从游牧部落雇佣骑兵或诉诸马匹贸易。根据马市记录,游牧民带来准备出售的马匹几乎总是远超农耕民族的需求量——如果可能,游牧民巴不得卖出整个草原上的马匹,再把换得的钱帛手工品散发到整个草原。通过代理马匹交易,卖马部落赢得游牧地区公认的权威性,而农耕社会的物质文化也渗透到草原深处。
农耕民族虽不甘于财富外流,但无论是不时爆发的战争,还是平日举行的狩猎、赛马和马球等活动,都暴露出国家马政成效的难如人意。这迫使他们服从马匹知识的势能差,不断从游牧民族那里寻求优良马种和驯养技术,由此形成包括作为物质的马匹、作为知识实践者的养马人和理论化的养马知识等不同层面的知识流动。
查费茨注意到,当游牧民族占领农耕区域建立王朝后,他们往往从卖马人变成买马人(229-230页)。这一方面出于把农耕文明的财富借马匹贸易向草原转移的思维惯性,一方面源于军队规模扩张导致的马匹紧缺,游牧帝国更清晰地意识到:骑兵的战斗力基本等同于坐骑的冲击力和耐力。当然,来自阿拉伯乃至法兰西的高头大马也远比蒙古矮马更讨得开过眼界的统治阶层的欢心。
第三,贸易者的逐利性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动力。
如前所述,跨区域马匹贸易在古代极为繁荣,而商人逐利本能使他们乐于充当知识中介,将各地养马良法介绍给潜在买家,某种程度上他们提供的技术服务比货物更有价值。例如穿梭于唐帝国与突厥汗国之间的粟特商人既卖马也卖马具、教授骑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向印度各邦提供战马时,同时传授欧洲的饲料配给和马蹄护理经验,以减少热带气候对北方马的不良影响,从而加强客户黏性,保证“回头客”。商人们还擅长“看人下菜碟”,给不同身份的顾客提供不同等级的马匹。在赫里德瓦尔等印度马市,披挂华丽鞍具的顶级马匹不明码标价,而是私下出售给特邀的尊贵买家(136页)。很显然,关于名马的产地、毛色、体格等鉴定知识,与印度人用来支付货款的各类宝石的评估知识同时双向流动。面对中低端的军用和大众市场,马商则采取规模经营策略,并运用对动植物季节周期和草场地理知识来让货物增值。例如阿富汗和中亚马贩经常低价收购体格瘦弱但具有潜力的普通马匹,在合适的环境中加以饲养调整,特别是在赶赴马市之前,要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草场休憩,给马匹“催肥”,转卖获利。
不同地区和人群对于马匹的具体偏好,也引导着育马知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地处半干旱平原的印度拉齐普特人喜好耐热耐渴的小型战马,而阿拉伯沙漠部落钟爱速度快、爆发力强的突击型快马。市场导向促使商人与育马者结合,运用愈发专门化的饲养训练技术,培育出具有重型战马、轻型迅跑马、长途耐力马等不同特色血统的纯种马。

辽代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博物院藏。
中世纪中叶可以说是“马背文明”主导欧亚格局的时期。在政治上,草原的征服者凭借骑术威震天下,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马背帝国。而马匹突出的流动性也为文化和知识体系带来了更多的扩张性。掠夺者和贸易者在文明间穿针引线,让草原与农耕不再是泾渭分明的“文明对蛮夷”的二分结构,而是在多孔甚至交融的边界双向影响。这一格局随着近代火药枪炮等新军事科技的兴起而发生扭转。欧亚草原逐渐被周边的定居政权瓜分。运输效率更高的蒸汽交通工具则让人类的物质和知识交换进入新的阶段。
尽管马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其传播史依然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早期范例和镜鉴,正如丝绸之路研究者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片土地曾是地球旋转的轴心”,马作为连接欧亚大陆众多文明的纽带是不应被遗忘的。《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恰打破了欧洲中心观的成见,弹奏了定居者与游牧者共同谱写的乐章。它让读者领略到,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孤立封闭的,知识和观念交流塑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主流和常态。另一方面,从古代的马匹到近代的蒸汽机,再到现代的石油和核能,驱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技术不断转型,其背后知识传播的结构与动力也在不断演化。查费茨的著作不但是对马曾经承载的文化交流的一曲颂歌,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交流互鉴、盛衰兴替的智慧启迪。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