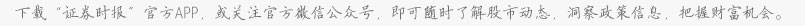成为一名作家,不仅仅需要热爱
- 外汇
- 2小时之前
0 - 3
杨婷
刘楚昕在漓江文学颁奖庆典上一哭成名,他的小说《泥潭》卖了80万册,书定价为42元,若刘楚昕的版税率为10%,则他每卖出一册可获得4.2元的版税,80万册的版税收入约为336万元。据悉,刘楚昕从2013年开始构思,2016年完成初稿,2024年才最终定稿,整个创作过程耗时十余年。从经济成本角度来看,很难精确计算他成为作家所花费的成本,因为这期间,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忍受着来自各方的痛苦和压力。
在我国,一个人想成为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是一个重要标准),需要多少成本呢?从最表层看,想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作家,需要出书,自费出书的价格约为5万元/本,加入中国作协至少要出3本书,共花费15万元,这是基本预算。若你矢志写作,你不仅要耗费时间(即时间成本),也要承担放弃其他工作的代价(即机会成本),还要接受自己或许不能从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因而湮没无闻的风险(即高风险成本)。如何应对高时间成本、高机会成本和高风险成本,是作家职业选择中绕不过的现实考量。
当作家最直观的机会成本是牺牲经济的稳定性。写作难以提供稳定收入,多数作家需要兼职维持生计。一位能拿到2万元月薪的广告策划人,若选择全职写作,可能面临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没有收入的困境。此时,机会成本不仅是每月2万元的固定薪资,还包括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职业晋升带来的薪资涨幅,以及职场人脉积累带来的潜在合作机会。
时间的不可逆分配,是作家最核心的机会成本。写作需要无干扰的深度投入,这种时间一旦投入,便无法再用于其他领域。一位每天写作4小时的创作者,若将这些时间用于学习编程,可能3年内成长为初级开发工程师;若用于经营自媒体,或许能积累10万粉丝的私域流量;若用于陪伴家人,能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此外,作家的时间投入,还存在“沉没成本”的风险:花6个月写的小说,可能被编辑退稿;花3个月打磨的散文,可能投稿无门,无人问津。这些无法产生直接价值的时间,若用于学习其他技能或拓展人脉,往往能获得更明确的回报。更关键的是,写作需要持续投入,像期货市场里不断追加的保证金——作家必须花时间阅读、观察、思考,甚至需要花钱去旅游、去采风、去考察。这进一步挤压了用于兼职赚钱、提升其他技能的时间。且此处时间投入具有不可逆转性,金钱投入具有天使投资资金的属性——一旦停止投入,创作便会枯竭。其他职业的技能积累,往往具有更强的可复用运用性,比如你学开车,一旦学会就一直可以开;你学会了游泳,学了就忘不掉,可以反复运用。但是,写作需要持续精进才能保持状态,每个有追求的作家都像西西弗斯。
深度写作需要独处,这种状态会自然减少社交频率。当朋友聚餐、同事团建时,作家可能正在赶稿;当他人通过社交拓展人脉、获取行业信息时,作家在看书码字、与自我对话。这种社交收缩,不仅意味着失去潜在的合作机会,还可能导致作家的生活与现实脱节。长期沉浸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对职场规则、人情世故的敏感度可能下降,若未来因创作遭遇瓶颈想回归职场,需要重新适应社会协作模式。生活体验的“选择性放弃”产生的影响同样显著:为节省开支,作家可能要对旅行、看展中的一些付费项目忍痛割爱,而这些体验本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为保证写作节奏,可能放弃稳定的作息,或者错过即兴的朋友聚会——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恰恰是普通人感知幸福的重要来源,却成了作家不得不做的牺牲。
作家还有可能因久坐导致颈椎病、肩周炎等,这是常见的健康损耗成本。
以上所有成本,都是“选择”带来的必然结果。作家放弃稳定的收入、自由的时间、丰富的社交甚至身体健康,最终兑换成了精神创造的独家性——用文字治愈自己、记录时代、表达思想、构建跨越时空的共鸣,这种价值无法用金钱予以衡量。此外,丰饶内心世界的灵魂自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风貌,也是妥妥的正收益。
正视各种成本,能让选择更清醒:它提醒每个想成为作家的人,这条道路不仅需要热爱,更需要对“放弃”的坦然,对“不确定性”的耐受,以及对“隐性代价”的清醒认知。毕竟,真正的作家,明知代价,仍愿为文字燃烧。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