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青云梯》:彩云之南的铁路传奇
- 外汇
- 1小时之前
0 - 4
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作家范稳写作了长篇小说《青云梯》。
《青云梯》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廉膺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关于创作缘起,范稳介绍:“1910年,法国人修通了滇越铁路,那是带着殖民强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背景的。当地人最初对火车充满仇恨,这种仇恨不是拒绝现代文明,而是民族自尊心受挫。”他提到,铁路的闯入让身处“人背马驮时代”的云南人看到了文明的落差:“一个马帮队驮运的锡矿,只能堆满火车车厢的一个角落。这时人们才意识到,火车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
压迫催生了觉醒。三年后,云南的士绅乡贤决定修建自己的铁路——“个碧石铁路”。范稳强调:“这是中国第二条自主修建、自主经营的铁路。轨距只有60厘米,时速仅15公里,但它象征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这条铁路成为云南人走向现代的“青云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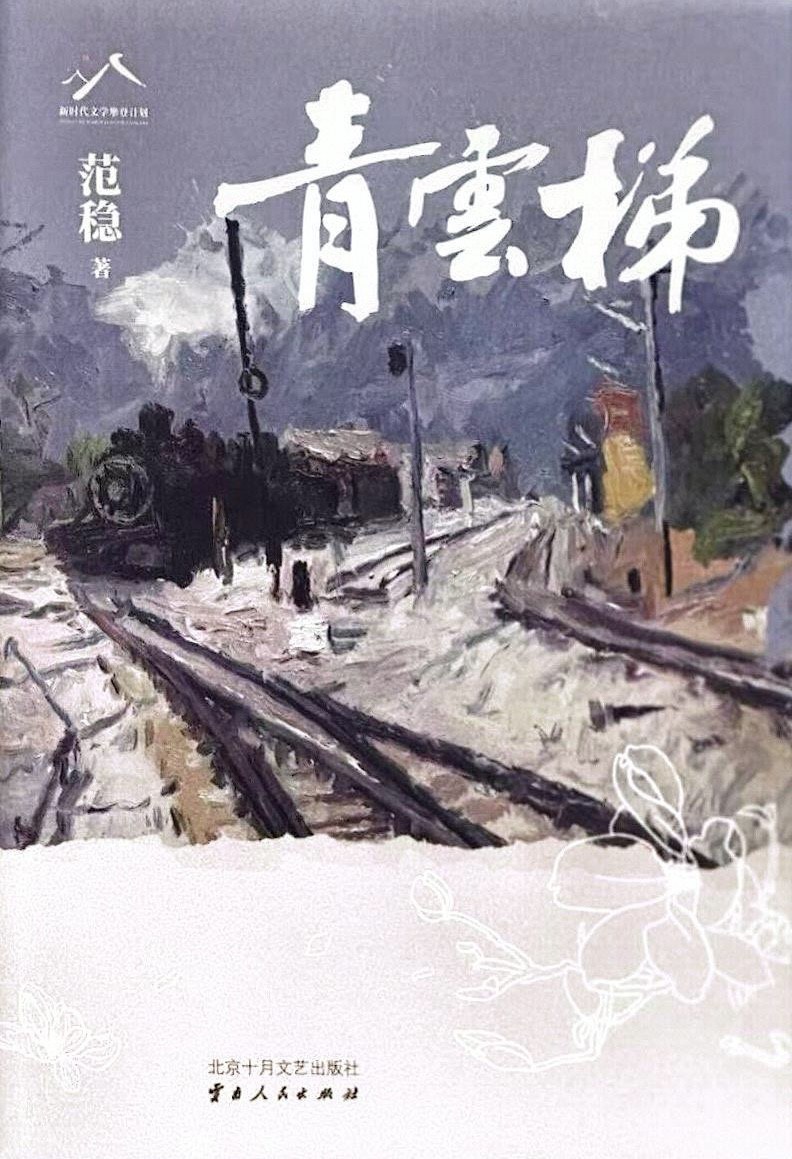 书影
书影不要坐在书斋想象,要以肉身丈量
范稳说出了大众对于云南一个普遍的刻板印象——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民族歌舞、服装、饮食琳琅满目,充满了异域情调。“但其实云南还有跟中原文化连得非常紧密的一种文化传统,现代文明的代表——铁路、矿山、公司等等,某些年代云南还领先于内地很多省份。”
为创作《青云梯》,范稳投入近四年时间,深入红河州的田野与史料之中。他介绍:“我的写作分为三步:一年田野调查,一年阅读构思,一年写作修改。”他走下矿井、探访铁路旧址、采访家族后人,甚至因各地热情款待“一路喝酒,喝到牙齿松动”。这些经历让他捕捉到文字之外的温度:“写小说最头疼的是细节。你坐在书房里想象的生活场景,到了现场才发现是错误的。”
范稳进一步补充了这些他意料之外的细节:“书中写到矿工在黑暗隧道中前进的场景,我最初描写他们‘举着火把’。直到我戴上安全帽跟着向导钻进废弃的锡矿坑道,才发现岩壁上全是放置油灯的凹槽。向导说:‘火把会消耗氧气,矿工只用小油灯,灯灭了就得往外跑——这是保命的常识。’这一笔修改,让整个章节的紧张感完全不同。”
“查阅滇越铁路史料时,我注意到‘咖啡’被频繁提及,但直到在碧色寨的老站房里喝到本地人用铁壶煮的咖啡,听他们讲述祖辈如何从厌恶到迷恋这种‘洋玩意儿’,才真正理解文化交融的具象体验——后来书中有一段描写法国工程师与中国工匠分享咖啡的场景,就源于那天的气味记忆。”范稳谈道。
除了这些物质细节和历史细节,一地之风物与文化,更需要亲自体认与感受。范稳在书中写过一场彝族婚礼,原本按照套路设计了欢歌笑语。但后来他在红河县一座山寨亲眼见到新娘哭着唱《送嫁歌》,歌词里全是对父母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恐惧。一位哈尼族文化学者告诉范稳:‘我们的喜悦藏在仪式里,但眼泪才是对娘家最真实的告别。’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是资料里查不到的。”范稳感慨。
这些真实的细节虽然弥足珍贵,但范稳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不要仅仅复刻现实,而是获得一种“虚构的底气”。
他以书中“朱家花园”的家族故事为例:“真实历史上的吴氏家族资料有限,但通过走访其后人,我听到许多关于‘分家产’‘送子弟留洋’的碎片化记忆。这些碎片像拼图,让我能够合乎逻辑地虚构出家族宴席上的一场冲突——读者觉得真实,主要是因为情感和文化的逻辑成立。”
 范稳
范稳“一个作家的写作就像登梯”
谈及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道:“在云南修铁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具象上也像架起一座云梯;而修铁路的人不断探索、追寻现代化的生活,胸怀青云之志,也蕴含着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气质。”
这种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也表现在范稳的创作过程中,从《水乳大地》到《青云梯》,范稳认为自己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是写得更慢,但是更自信了。“更慢”是因为“要不断地查资料,一字一句,字斟句酌”,“更自信”是指“通过对地方文化的学习,在写作中,可以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触类旁通”。
书中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朱家花园(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作为叙事支点:“朱家是读书人出身的矿商,他们有家国情怀,修铁路是为民族争一口气。但再多的财富也抵不过时代洪流,家族由盛而衰的命运背后,是云南近代史的缩影。”
范稳的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他也著有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长篇小说《碧色寨》和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