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风雨故人来
- 外汇
- 昨天 13:50
0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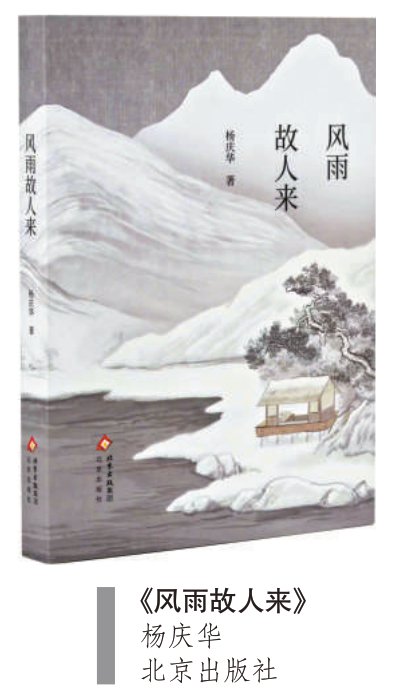
▌杨庆华
我的上一本书《风雨艳阳天》讲述1949年之后我国文艺发展的风雨历程,是2016年8月至2020年3月写成的。当时我和责任编辑约定,接着《风雨艳阳天》,再写一本新书,写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与写作。五年过去了,迎来了这本《风雨故人来》。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此书收入的三十二篇读书随笔,绝大部分写于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它们是个人的阅读感情和理解,是向经典致礼,也是对往日的一点纪念。
这两三年,读书陪我度过这特殊的岁月。我把几十部文学名著重读过一遍,感受十九世纪小说家的真实生活,重新回到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当从头再读冉·阿让的故事时,我再次体验到了《悲惨世界》最初带给我的温暖与欣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我还在上中学,为了购买《悲惨世界》第五卷,我经常去新华书店打听出版消息。那时是翻译文学的黄金年代,阅读外国文学是一种风气。
十九世纪的小说成就太大了,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分别出版于1811年和1813年。1831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司汤达的《红与黑》出版。1834年,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问世。1838年,狄更斯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奥立弗·退斯特》(《雾都孤儿》)。1844年,大仲马写了《三个火枪手》。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出版。1857年,福楼拜出版第一部作品《包法利夫人》。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1869年,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91年,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出版。
那个时期也是译制片的黄金年代,译制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由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赢得了观众的青睐。我记得很清楚,198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译制片《蝴蝶梦》上映,5月1日下午,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走进农展馆影剧院,电影里的曼德利庄园让我魂牵梦萦。我至今怀念银幕上的琼·芳登和劳伦斯·奥利弗,怀念配音演员向隽珠优美甜润的声音:“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利。”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流动着对当年读书时候的往事回忆。那些“基度山伯爵”们、“安娜·卡列尼娜”们、“雾都孤儿”们、“包法利夫人”们,把我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神奇的历史深处,和狄更斯小说中的奥利弗和皮普一起体验19世纪伦敦市民生活,或者到马赛,感受爱德蒙·邓蒂斯的报恩与复仇,文学给我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
到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里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奠定了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写作《风雨故人来》将近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写,一边看书,重温那些影响我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学经典,仿佛故人重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完一集邦达尔丘克改编的《战争与和平》,再返过去细读同名小说,与远在童山村保古察罗伏大庄园的安德烈对话,跟着托尔斯泰一起迈上遥远的旅程。巴金说:“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