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红学” 简化“红学”
- 外汇
- 2小时之前
0 - 2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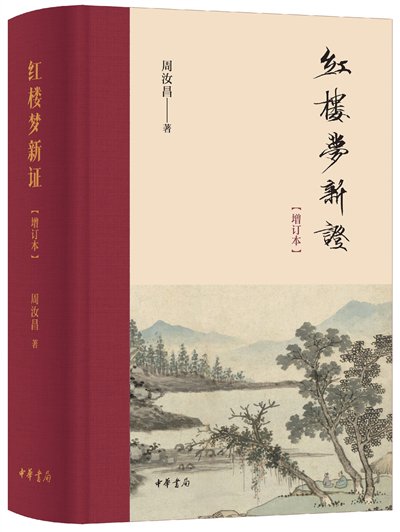

普及“红学”,不是让每个人都做什么红学家。简化“红学”,不是要将一门学术弄成“简单化”。人人都做红学家,就是说说笑话。将红学简单化,就是将它庸俗化——实质上是消灭了它。
那么,为何要普及它?
因为,凡为中国文明人,都应知道这部民族骄傲的名著的基本情形。因为,如不普及,它就会为极少数人私有——这私有,就成为他们少数几个人的“专利”,不许他人染指,只许为他自己营造私名私利。
如何方能又简化,又不致流于庸俗化呢?曰:这其实不难,不麻烦,只需掌握一把钥匙,即可门径咸通——这钥匙,作者曹雪芹开卷就已交付于人们了。无它,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十个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就是说,“红学”者,正是要一面理解其“荒唐”字面,即“文本”表层;同时又要一面思考、感悟其内中所隐藏的“辛酸”泪的实情实际到底是些什么。
“红学”之所以为学,正在这种好像“负阴抱阳”般地将表层与内涵二者“矛盾统一”起来,从而获得雪芹所感叹的“谁解其中味”。
要解说“红学”可以千言万语,专文大著;然而要“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上文所述的雪芹本怀,并无别解。
然而,世上不止一位大学者天天在那儿痛心疾首,感叹红学进入“死胡同”——脱离了“文本”,脱离了“文学创作”,将“红学”全“变”成《红楼梦》以“外”的什么考证、探佚等等,云云。换言之,他们实质是主张雪芹的艺术特点并无任何特点可言,他的“文本”并不具有表层的荒唐与内藏的辛酸,他所说的“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什么“细”?什么“味”?都是废话连篇,你只要看“文本”就是了,何必都去思考、探佚、感受、领悟?那都是“文本”所没有的。
是这样的吗?
那答案若是个“是”字,可就真是太“简单化”了。《红楼梦》那么“简单”呀,无非一男二女“争婚”,“爱情”之“悲剧”呀,有何深奥意可考可证?
这也就无需再讲什么“普及”了,大家彼此一笑罢休可也。
世间的事,常常妙得很,比如,有的大学者,自己不肯,又不会、不屑做“考证”,只把别人的考证成果当他的“常识性知识”来对待,然后大声反对“考证”——把“考证”与“文本”对立起来,视为“势不两立”的“天敌”。似乎“考证”独存,“文本”已灭……堪忧者怕呀!
总之,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不寻常的,大大胜过我们平民百姓、粗识“之”“无”之辈。
毫无疑问,“红学”还需要从根本上普及,也需要按照雪芹本意实情那样的“简化”,即紧扣“荒唐”与“辛酸”之间的深刻内涵大旨。
(本文由周汝昌之女周伦玲新近发现并整理——编者注)
